1000小食报 #12 储藏食物也是储藏我们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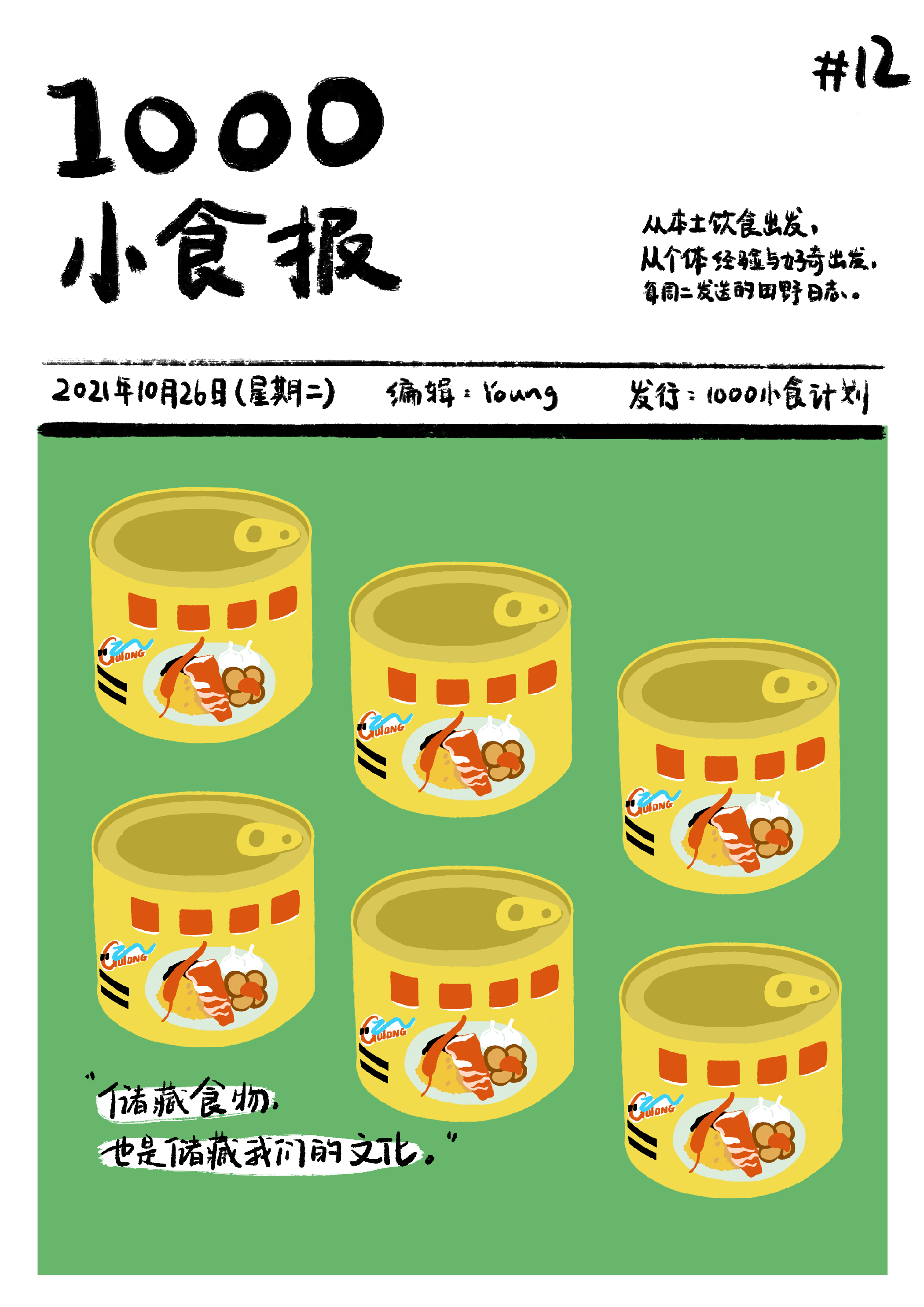
上周和一位即将离开北京的台湾朋友吃饭。吃饭前,她从包里掏出两盒罐头赠予我。罐头是新东阳的「红烧小卷」和「红烧鳗」,因为要清空在北京的住处出发旅行,她只好把这些从台湾背回的罐头散发出去。饭桌上另位朋友也回忆起自己的台湾友人临别也留下过罐头。
我又回忆起,以前和这位台湾朋友共事时,她从家给我带回过很有本土味道的一夜干(用盐水腌渍一夜风干的鱼)和剥皮辣椒。
罐头、一夜干、剥皮辣椒,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能将家乡味道长久封存的储藏食物形态。前美国驻华使馆行政总厨、广州“朗泮轩”中餐厅的创始人罗朗,在一席讲述他的中餐学厨历程和对饮食文化的根源思考。在精进厨艺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是在中国各地人们储藏食物的习惯中获得料理启发:
我发现对于我来说,食材烹饪的技巧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人们是如何储存食物的,比如那些腌制的、泡的、晒干的、熏的这类东西。这是我们最古老的烹饪方法,在没有高科技之前,我们就是要靠大自然里的东西才能生存,才能吃饱。全世界各地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发现,动物是可以驯养的,我们是可以控制这些食物的新鲜度的,比如腌制、晒干食材,或者通过酸面,用发酵的方式去保存食物,而且可以增加它的营养,对身体很好。那就是文化,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文化的来源。
文化不单是看的,或者是听的,文化也是吃的。当人们在做这些储存食物的活动时,他们就是在动着的文化、活着的文化。

台湾朋友赠予的「红烧小卷」罐头

「香菇肉酱」和「牛奶花生」
朋友临别赠予的罐头牵连起我的罐头记忆。最有代表性的,也在许多福建人味觉记忆中会留下的应该就是古龙牌「香菇肉酱」和银鹭牌「牛奶花生」吧。
前者出现在我童年的画面,是在冒着暑气的清晨,早早上班的父亲独自坐在饭桌边吃稀饭佐香菇肉酱。因为罐头的滋味浓厚,夹一小簇肉酱入口,需要拨两三口稀饭冲淡滋味。一粥一酱便是一顿极简的早饭。
童年的我并不能领会这款罐头的美妙,一来小孩对浓郁的酱油豉香并不感冒,二来会对混沌一体不辨食材形状的肉酱保持着警惕。直到有次我体会到从肉酱里抠出完整一块肉的快乐——大概自那以后,父亲吃到的香菇肉酱真的都只剩肉酱了。
因为这个罐头过于日常,我甚至没有注意它什么时候从我的生活中离开。今年初父亲说自己一个人吃早餐的话就不怎么费心,吃得很简单,我才想到在某宝搜索这味香菇肉酱给他寄去。还惊讶地发现,十几年时间里这罐香菇肉酱的价格竟然只微涨两元。
我想有很多属于本土的味道是像「香菇肉酱」一样,在我们成年后回过神才品出滋味的。
循着回味搜集资料,我发觉这罐头里封存的不仅是我们的味觉记忆,还封存下一段闽南在地历史。
厦门沦陷,日本侵略者横行鹭岛,数以万计的难民涌到鼓浪屿避难。彼时,一个由11名中外人士组成的“鼓浪屿国际救济委员会”迅速成立,负责难民的安置和维护秩序工作。除了工厂、教堂、寺庙和学校外,鼓浪屿人也纷纷伸出援手,把私人楼房腾出来供难民住。
难民居住基本解决了,但吃饭是个大问题。“难民们生活无着,三餐不继,淘大公司内厝澳工厂用加工罐头菜料的大锅煮粥施赈,为期数月,救人无数。”彭老口中说的淘大公司,是一家华资罐头厂。
「古龙」和「银鹭」都来自厦门。古龙并非武侠源起,而是厦门鼓浪屿的「鼓浪」谐音,古龙食品公司即原来的厦门罐头厂。厦门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7 年由爱国人士与华侨在鼓浪屿创办的淘化罐头厂,也是厦门罐头厂的前身。
考古资料,还看到有人从古龙罐头的包装细节梳理出一条品牌的发展脉络,也反映出不同时期中国的文化经济特征,很有意思:
如果注意看老包装上的英文可以发现, 福建的英文是 Fukien,厦门的英文为 Amoy。Fukien 是“福建”邮政式拼音的旧拼法。Amoy 是“厦门”的 英文旧译,大部分人认为是源于“厦门”的漳腔闽南话发音。Amoy 自 19 世纪中叶起使用了超过百年,一直到 1978 年汉语拼音成为我国地名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后,才逐渐被 Xiamen 代替。

厦门罐头厂出口的罐头包装
这些出口罐头的平面设计,今天看来也很赏心悦目。早期罐头上的食物展示均以插画表现,后期才采用的摄影方案。有意思的是,小时候我总盯着香菇肉酱的包装上那张装着五花肉、香菇、黄豆的盘子照片,竟然就是依照早期插画所拍摄的。

大到产业,小到包装细节都被好好延续下来的古龙罐头,可以说是真正「长效」的设计吧!
相较古龙,于 90 年代出现的银鹭「牛奶花生」则年轻许多。牛奶花生源于福建传统的甜汤花生汤。所谓「牛奶」不过是兑入了乳粉,但在 90 年代,带有牛奶字样的食物就会给人多几分营养的错觉,所以爷爷家经常会收到访客提来的一整箱「牛奶花生」。
也因为爷爷的缘故,它成为我记忆中即食点心的代表。在我出生之后,爷爷从医院退出开始经营家里的中医诊所。为了平衡大家族的生计和自己近八十岁的高龄身体,诊所只在上午接诊,看完最后一位病人时往往都过了午饭点,所以上午一旦有空隙时间,父亲就会倒一壶开水,把牛奶花生罐头浸入开水加热一会儿给爷爷做点心吃。小时候我被托管在诊所时,常常能蹭到不少爷爷的点心。
现在看牛奶花生就是 90 年代的「速食」。毕竟制作福建传统的花生汤也是很花时间的:花生煮熟后手工一颗颗脱皮,再用高压锅将花生汤压制软烂,但花生还保留着完整的颗粒。福州人称「没牙伯」花生汤,就是因为花生入口即化,连没有牙齿的老人也能吃。

上期邮件中提到家里给我「寄汤」,其实除了父亲的牛杂高汤,有时候收到的包裹里还会出现母亲的花生汤——这是不擅厨事的母亲最擅长的一道小食。
回到 90 年代,那也是一个大众传媒兴盛的时代。在搜索牛奶花生的资料时,我猜测银鹭早期的广告投放或许也是让这个罐头占据福建人心智的重要因素。在那个年代,有谁能不在「给我一个吻」的广告音乐中陷入一口香甜念想呢?
还注意到时间最近的一条新闻是 2020 年底,雀巢集团将银鹭食品剥离出售,而收购方 Food Wise 的控股方正是银鹭创始人陈清水家族。粗略将银鹭的时间线勾勒出来就是:80 年代创立,90 年代兴起,2000 年初快速增长,2011 年雀巢收购 60% 股份,2018 年成为雀巢全资子公司,2020 年又被出售给创始家族……
这些深藏于家庭食品柜里的罐头,无论是鼎盛还是衰微,都在默默记录着历史,一打开都是时间的故事。

传统花生汤的制作过程

中国的「食育」
2017 年我在硕士毕业论文的后记中写下这篇从「食欲」到「食育」。当时所提的「食育」并非狭义上在日本和欧洲已经比较成熟的面向儿童的教育理念方法,而更接近一种自我教育、或者说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一周前我有机会接触到在中国儿童中心里的一间「食育课堂」,我才好好了解了一下狭义上的「食育」所指,并且观摩了一场真实的食育课堂:
这个名叫「豆豆街」的食育课堂每学期由中国儿童中心对外招生,上课的小朋友主要年龄段分布在 5-10 岁。以秋季学期的课程为例,课程以「蔬食」为主线,结合中国的节气安排每周主讲的食材。每堂课时长 1.5 小时,分三个环节:知识点传授(主要以营养和文化知识为主)、感官体验(现场让小朋友观察、触摸、品尝一种食材)、烹饪实践(每节课都会由小朋友亲自按照指导步骤完成一道料理)。我所观摩的这节课是围绕「霜降」节气食物所展开的,老师讲解了霜降的原理、霜降蔬果的糖化原理,接着教小朋友制作了「萝卜肉丸汤」,又包括切萝卜、肉馅调味和挤肉丸。
现场制作完的萝卜肉丸汤,小朋友们都会用自己的饭盒装好带回家。我问食育课的老师,他们都不会想自己先尝尝吗?老师告诉我,小朋友们都更愿意带回家跟家人分享。
后来和食育课堂的老师询问课程设计的逻辑,也提出了我在了解其他各国食育案例后的问题:
日本的食育贯穿人的生命全程,芬兰的食育课会通过食物传递人的「平等」,法国的食育培养对食物的品味,意大利讲慢食,德国在解决剩食问题……
那么,中国食育最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还有能支撑起中国食育理念体系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在现实的探索尚且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都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想食育的范畴或许不应仅限于受教育的年龄段,食育的问题也不局限于教育者、抚养者来思考。以我自己了解本土饮食的过程和获得来看,这也是一种食育。


独立出版《te》第一期:失落的协会
“失落”并不指失去和消亡,而是暂时的沉寂与失势。
在这一期里,我们邀请了13位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以食物的角度切入人类学、社会学、当代艺术的流变现象并进行反思,旨在揭示食物在不同研究动线中附着的多重概念,同时也将食物与地缘的关系打破重组。
Young:计划这周去上海艺术书展 UNFOLD 现场购买这本新刊。将这段介绍摘录出来时,我想罐头或许也只是暂时的「失落」——它本质上是储藏、即食和便携,这简直是捍卫人生存底线的强悍存在。比如台湾的食物设计师陈小曼受农作物因气候极端而过产与不均的问题启发,发布了自己的罐头食品品牌 LOUU:
《專訪食物設計師陳小曼 — 味覺的審美改造,從罐頭開始》
《现地热炒》和《飯丸》
吃熱炒就是要坐矮凳,但到底為什麼是矮凳呢?
對喝酒的人來說,離地板近一點,喝醉跌倒時也少痛一點
你覺得熱炒提供矮凳的原因是什麼呢?
https://www.facebook.com/projectinsitu/posts/2251630391721759
Young:这是两本立足于台湾本土饮食形态(台式热炒和饭团)的独立出版物。关于创作过程可以听播客「新鲜知食」中的这期节目。

《饭丸》的装帧设计采用了满版打凸来模拟干米饭的触感
为了做传统「佛跳墙」拍了五天视频
Young:川菜厨师王刚按照古法复刻了闽菜中的「佛跳墙」。看完视频的最大感受是,佛跳墙的贵价比食材要贵的是时间。泡发和煨汤(分头汤、二汤和最后出品会黏嘴的金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起一锅汤就是七八个小时,把食材完全泡发就得两天。视频中有时候一天的拍摄就只有把鱼翅、鲍鱼从泡了一天的清水中取出,焯水一道再浸泡的步骤。没有捷径,只能等待。
贤者时间:当我切土豆时,我就只在意土豆
Young:与食物有关的一期温暖诉说——不是抒情,而是将记忆中与食物和人有关的细节轻轻抖出来:比如为了一解治治在疫情期间对炸鸡的思念,妈妈做的「炸鸭」;比如小张给治治用电饭煲煮红酒,开锅只剩下一颗橙子肉桂和八角……刚开始听是笑,在笑意还挂在脸上时鼻头就开始发酸。
播客的主播小张在节目发布的即刻动态里写道:
当我疲惫,我就白灼一切
这让我想到作曲家 Timo Andres 在采访中被到是否会按照菜谱做菜,他的回答是:
I choose a process, not a recipe.

截至本期,写 newsletter 也坚持满满三个月了。最近的一个新体会是,有很多记忆的细节我是在书写中捡起来的,它们甚至是我在起笔时都不会料到的出现。
这几周也常常是半夜写信,从凌晨三四点一直写到天亮(往往星期一晚上会先睡个短觉)。在这样的时间,无论是在实体空间还是网络上都安静得像个空白编辑器,而自己也因为已经睡过一觉,淤积的思绪也被清空,开头也会轻盈一些。
写信时间调整造成的一个不太好的结果,就是周二的投递时间总在变化(但还是会坚守住周二)。
上周日还算正式地跟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室—— Young Clinic,这是一个探索本土饮食传播的创意编辑室。具体会包含哪些业务,大家可以在文章中查看。
在这期的田野手记中,我也提到了爷爷的「诊所」,而 Young Clinic 也是我对家族传承的一种回应。

由 Young 编辑的《1000小食报》:
查看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