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小食报 #17 菜市场教会我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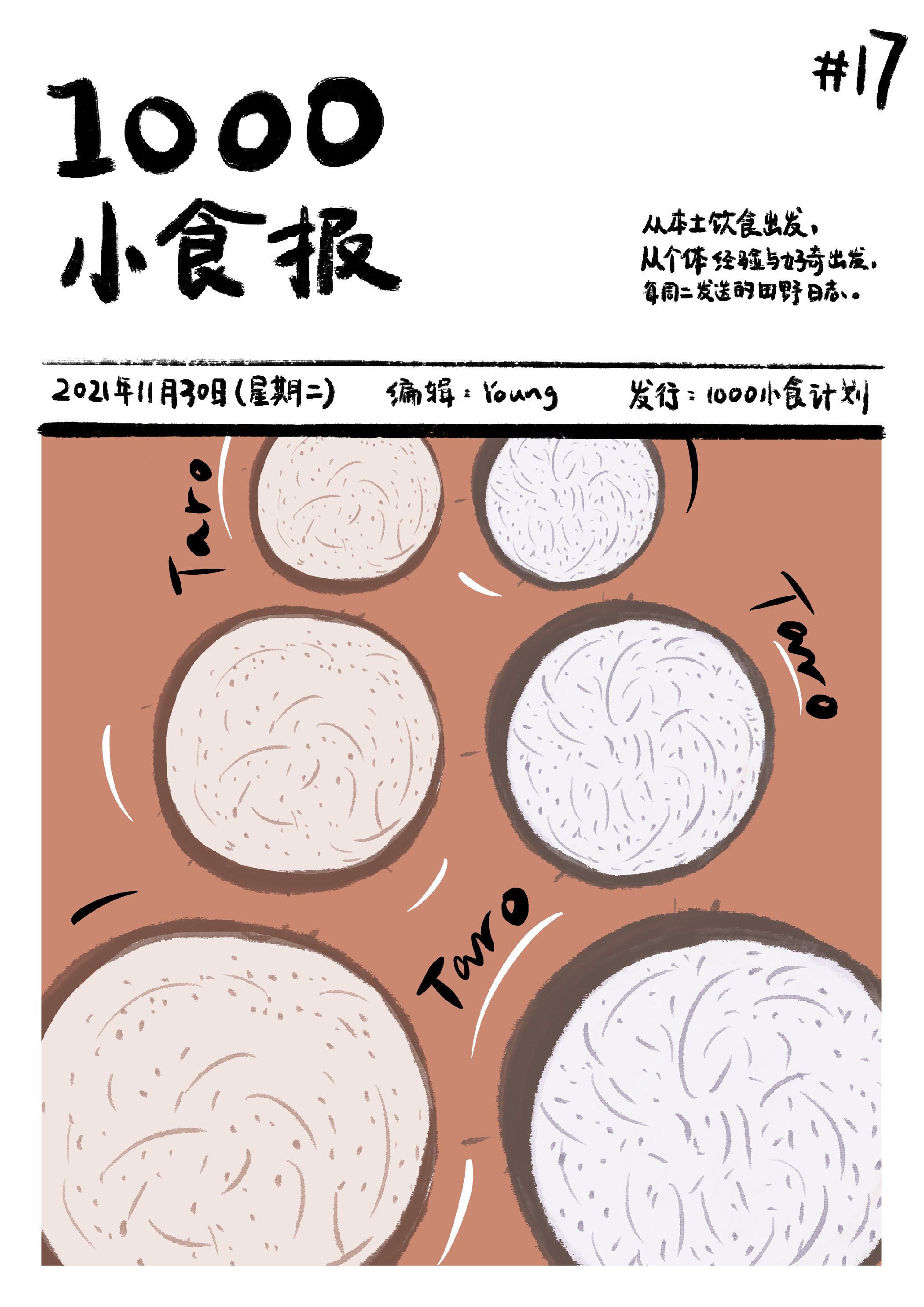
准备这周的小报时,我感到有点难以着手。
单把这一周的时间表拉出来,就包括参加了两档播客节目的录制、和餐厅经营者去农贸市场采购食材、也和两位有截然不同背景的餐厅前主厨对话交流、还有穿插在日程中的零碎阅读、拆箱、实验和品鉴。能够集中思考和书写的时间很有限。
最近的两次饭局上,有前辈得知我在更新这份小报,便询问每周的写作是否会按照某个体系进行规划,或者是否会如美食自媒体一样将自己的美食经历予以分享。我知道用「美食写作」或「美食自媒体」这样的说法能更快回答人这份小报的内容指涉,但我还是会诚恳地慢一点跟人解释它的意图,以及从书写角度与这二者的分别:
《1000小食报》完全是从我的好奇出发的,或者说是从我对本土饮食所抱有的问题出发的,即本土饮食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应该如何在当下延续。这个「当下」的背景是与我同时代的年轻人、新一代年轻家庭所建构起的生活方式。我隐约感到现在所追求的种种,与根植于本土的传统饮食形态渐渐相去甚远:于文化而言它将失去传承,于我们这代人而言,则是失去根源和差异。
为了延续本土饮食,首要去做的还是记录和身体力行地学习,在理解根源的基础上再发挥创造性,寻找与当下的沟通语言——这会是个漫长滋养的过程。从我的体验来说,每一次围绕本土饮食记忆与技艺展开的交流都会带来新的洞察和新的好奇,让记录本身成为了一件富有生命力的事情。
回顾这周与餐厅经营者和料理人的对话,留下来最重要的一个感受是:理解本土饮食,是从理解食材开始的。

南方来的芋头
海元哥是江苏南京人,他的爱人是在桂林当地菜场里长大的。2016 年,他们在北京 798 开了「肆喜」的第一家桂林米粉店,最初的契机其实就是夫妻俩想在北京吃到家里的味道。记得朋友第一次带我去「肆喜」吃粉的时候,特别嘱咐要点一份红烧肉,因为这是海元哥跟外婆专门学来的苏式红烧肉。
到今年,海元哥在北京开了四家「肆喜」,分别位于 798、西单、十里堡和东四。这周我跟海元哥采购完食材,他把我在东四环路边放下便继续绕环路把食材输送到各家店。他说当年刚来北京时,也觉得北京很大,但现在因为常常自己跑采购,感受上的北京也就没那么大了。
「肆喜」的芋泥
8 月份一天,我去了刚开业不久的东四店,因为已经吃过晚饭,就只点了一碗绿豆薏米糖水,加芋泥。我很喜欢「肆喜」的芋泥,与家宴的「福州芋泥」和奶茶里芋泥都不同,它既能在糖水里保持独立的口感,还带着浓郁的芋香和细密的甜。
海元哥一边忙着照顾客人、拼配糖水、抽空就坐下来和我聊天,问我的近况。当我们聊到本土食物的传承,他说自己第一次有意识要将家里老人的手艺接管下来,是因为父亲的意外离世。在那之后,他跟母亲学红薯丸子、跟外婆学红烧肉、学江苏当地的纳豆做法。
纳豆在我的印象里,完全是因为小时候看的动画《蜡笔小新》,而听海元哥说了我才知道这其实是种中国食物。他的外婆利用田里的稻草来让纳豆自然发酵,还需要用菖蒲叶包裹。当地人食用纳豆的场景是加一点青蒜,配粥一起送饭。但是发酵食物在城市厨房里并不容易实现,比如他有回为了制作黑蒜,在家用电饭锅不断电地连续焖上两周,才完成的发酵过程。
这家广西米粉糖水店里的芋泥,引发了我对荔浦芋和当地芋泥做法的好奇。与福州芋泥使用槟榔芋,再混入猪油和白糖的做法不同,海元哥告诉我,芋头买回来先放一放,脱点水「糖化」,这样芋泥本身就会带着甜,也可以「减糖」。
不久后,店里收到荔浦寄来的新芋头,海元哥就联系闪送寄来给我尝尝,还担心我处理芋头太麻烦,就让嫂子都先削皮切好给我。亲自料理荔浦芋的感受是,它比我印象中处理槟榔芋泥要省力气,但如果要把这两种芋头的分别弄得更明白些,我还是应该去趟菜场。
大洋路海鲜批发市场
一周前我联系海元哥,提出想跟他一起去农贸批发市场采购一趟的请求,顺便也买点槟榔芋回来对照。
早上 7 点,他在东四环的辅路边接上我,开车不出 20 分钟我们就进了批发市场。
海元哥跟我说:「菜市场教会我很多。」
跟他进行了一趟日常采购,我对这句话有了些更具体的理解。
菜市场教人看待食物和生意的方式,不是菜单上的一张图、一句文案,是从食材出发的。

进入市场后,海元哥先带我去的水果区,从广东湛江的店主那儿采购了做糖水的凯特芒和木瓜。接着是去熟食区买米粉中加的豆泡和馒头面点——这是给店里北方员工准备的员工餐主食。
在熟食区路过羊杂卤货,海元哥告诉我现在就连一些羊杂汤店,都是用这种熟食直接切配后出品给客人了,由此感叹道「以后在餐厅能吃到别人为你亲手制作食物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了。」
出了熟食区,又在市场里一座独立的销售点购买了豆芽,接着是去酒店用品区买了店里要用的胶带、垃圾袋;最后又到了一排集装箱和小卡车聚集的片区,这里主要销售南方的蔬菜。
我跟着海元哥走进「32 号」集装箱,里面堆放着一座南瓜小山、一座山药小山、还有两座芋头小山。卖菜的是位北方大哥,在他口中没有「槟榔芋」的说法,只区分广西来的芋头、福建来的芋头。
广西来的芋头就是荔浦芋了,每一颗椭球体都套上了泡沫网袋,大概按七八颗装在一个塑料箱里,塑料箱堆成一摞。而福建来的芋头,个头更大,整体呈圆柱形,长约 30-40 公分,所有的芋头被塞进一个超大的编织袋里,从袋子里漏出来的四五颗芋头也直接放在了地上。

图:采购荔浦芋和槟榔芋
我询问大哥价格,荔浦芋 6 元一斤,槟榔芋 4 元一斤,他或许是为了让我确信荔浦芋更金贵好吃,还交代出有的奶茶店会将两种芋头粉对半掺以平衡成本的做法。最后我当然坚定地带走了一颗槟榔芋头。接着海元哥又带我找到整个市场里另一家有卖槟榔芋的卡车摊,摊上有一位老奶奶,见我在看地上的槟榔芋,笑着说这个芋头很好吃。
相比较上一间的大哥,老奶奶的话让我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受。海元哥指着荔浦芋接着问奶奶:「那你有没有尝过这种呀?」老奶奶有点不好意思地摇头。「这种贵的你也尝尝嘛,也很好吃的」,海元哥虽然口头还是站住荔浦芋,但他也从奶奶的摊上买走了一颗福建芋头、一颗广西芋头。
市场的最后一站是一家粮油店。除了要亲自采购确认品质的食材,「肆喜」大部分要用的食材都已经有了稳定的供应关系,直接联系各家摊主,按照固定的采购标准送到粮油店门口,最后一起装车送回店。比如店里卤制用的牛腩肉,卖肉的摊主自己也经营着四五家火锅店,所以大部分食材都往自己店里送,但也因为长期建立起的关系,他会单独留出一批品质上好的牛腩给海元哥,甚至还会比预订的量多称几斤。
还有炼猪油用的猪板油,海元哥店里也要挑几乎不带血丝的板油部位,说这样熬出来的猪油洁白如雪。我问他,那我自己去市场要怎么挑呢?他的方法简单直接,「你就告诉老板你要最好的猪板油,见过最好的是什么样子,之后对比就知道了。」
等大哥们把几十种食材依序严丝合缝地装进车里,这满满当当的画面与被当做「快餐」的桂林米粉和「小吃」广式糖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一家餐厅在追求品质的前提下,快餐其实不快,小吃也不小:单是作为糖水佐料的芋泥,就需要芋头经历由南至北的山高水长、时间里的自然糖化,最后才是手工的制作(此前探讨过为什么芋泥不用家庭料理机处理,上周父亲制作芋泥时真的尝试了一下,就发现芋头淀粉的黏性很快就会卡住刀片,动弹不得)。
回到厨房
星期四采购回芋头,昨晚(星期一)切了一颗荔浦芋和一颗槟榔芋来解答:荔浦芋和槟榔芋到底有什么区别。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种说法是,二者只是叫法不同,口感味道都相近;就连最近一次父亲给我寄的芋泥,也不再是用槟榔芋而是荔浦芋做的,说因为后者口感更粉糯。
出于对本土食材的情感和实践态度,我还是想自己对两种食材做些区分。
对比之下,两种芋头的外观其实就有挺大差别的,槟榔芋更接近圆柱形、荔浦芋更接近橄榄形。关于芋头形状上的成因,我在「台湾美食技术交流协会」的 Facebook 上看到的一种解释是受土壤影响:
一般而言,以水耕法在壤土種出的芋頭形狀圓錐,以旱做法在砂質土種出的短圓。這和根莖類植物在土中成長時受到的壓力有關。
芋头属于水田和旱地都可以种植的农作物,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气候条件限定了芋头主要在南方食用。曾和一位家乡河北的朋友聊起芋头,他告诉我自己第一次从市场上买荔浦芋来吃,是把它同理成「板栗烧鸡」这道菜里的板栗来使用的。

图:槟榔芋和荔浦芋的大小、形状对比
两种芋头切开后看剖面,荔浦芋是细密清晰的紫色纹路,槟榔芋的芋肉更白,枣红色的纹路较淡、也没有荔浦芋的纹路密集。用刀纵向削芋头皮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槟榔芋需要削去更多的芋肉部分才能看到纹路,而荔浦芋基本把褐色表皮削净后,就会看到芋头纹理。
所以从耗材的角度,尽管荔浦芋的市售价格较槟榔芋更高,但如果使用口感更好的槟榔芋心制作芋泥,投入的成本应该是比荔浦芋有过之无不及的。

图:槟榔芋和荔浦芋截面对比
将两种芋头切块上锅蒸熟,10 分钟后荔浦芋块已经完全粉化,槟榔芋块也可以用筷子轻松捅透,但靠近表皮的部分仍未松化。又蒸了 5 分钟后,夹出两块芋头分别尝尝:两种芋头入口后都是用口腔上颚抵住就松软的程度,但是槟榔芋水分更足,绵软好吞咽;而荔浦芋的水分少一些,粉化程度更深,需要与口腔里的唾液混合后才好吞咽下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此前我在用荔浦芋做芋泥的时候,感到比记忆中要轻松些。
再从香气和口味来对比,不得不说荔浦芋的香气更突出,不过香气和味道中都可以辨别出一种淡淡泥土清香,槟榔芋的香气和味道相较之下就显得更轻柔一些,没有任何泥土味道。如果空口吃蒸芋头的话,我还是会推荐槟榔芋。

图:用筷子捏出两块芋头的截面,也可以看出两种质地的分别
从食材理解本土饮食
在第 9 期小报里,我记录下我对福州芋泥的味觉记忆及其承载的情感价值。而坦诚地说,我对传统芋泥中的油脂和糖是有所忌惮的,如果不是朋友们聚会或归家的宴席,我也不会贪恋芋泥的味道。
做芋泥为什么要放那么多糖和油,有多少分量其实是超出了「好吃」的范畴呢?
本土的芋泥有没有变好的空间呢?让它不是仅仅存在于过节时的谨慎「一口」,而是在我们日常中的一种香甜记忆,既让我们想起过去对丰腴和甜的喜好,也会更长久地将它作为陪伴我们的文化载体。
仔细了解芋头后,也产生了一些从食材角度对本土饮食延续的思考(和问题):
- 槟榔芋是本地出产的作物,水田旱地皆可种植,根茎硕大,存储期长。这些特征决定了它在本土饮食中的应用广泛,也是一种本土主要的淀粉来源。
- 福州芋泥作为闽菜经典,首先得肯定它确实是对本土食材特性的一种极致呈现。优质的槟榔芋淀粉含量可以达到 60% 以上,如果使用传统烹调中的燉、炒,容易造成淀粉糊化。因此槟榔芋的使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做成芋泥,芋泥又分为宴席菜肴和小食两类,小食里的芋泥往往是作为馅料,比如「炸芋枣」;第二种是炸食后作为烧菜燉汤的辅料,既吸附油脂也让芋头本身滋味更佳;第三种是将芋头碾成芋粉或切芋头丝,同米粉混合做糕点或包馅的皮。
- 芋头的本味甜咸皆宜,而不同地区的口味选择透露出不同的饮食偏好/执念。比如在父亲眼里,芋泥的好吃取决于口感要够细腻,其次才是甜。而在《厦门饮食文化》一书中记载到厦门菜里的芋泥,有甜上加甜的「柿霜芋泥」,也有在芋泥中包入咸鲜食材的咸甜搭配「香泥藏珍」,往南到潮州用葱油替代猪油炒出「福果芋泥」。而在广西、湖南出产荔浦芋/槟榔芋,则直接用来同肉类一起蒸,如香芋扣肉和芋头蒸排骨……
- 芋头的甜和咸,二者在好吃的追求外,甜有时候是一种意义的添加:甜是珍贵的、是占有权力的、也是一种情感的代表。如果把意义保留,把甜味减去,芋泥是否也是芋泥呢?
- 芋头不能少了油,除了要中和淀粉质地外,之前忽视的一点是芋泥中的猪油有「保温」作用。芋泥作为一道热食的甜点,保留视觉和口感的反差确实别有心意,但有没有其他保温的方式呢?
- 对比荔浦芋个人感到还是槟榔芋更适合芋泥,虽然口感上不及荔浦芋的粉感,但如此需要添加的油脂分量也可以减少,以及降低甜度后能让芋头本身的风味更突显一些。
- 传统宴席上的出品方式就是一整盘,每人 kuai 两三勺分食完毕,但如果作为日常饭桌上的一道点心,什么样的份量和出品形式更合适呢?

受限于自己的料理经验,我也想将上述问题开放出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尤其是具有一定料理经验的朋友。期待能够一起交流、一起动手。
最近新结识一位朋友 Tongtong,在上期的小报中提到她曾经在伦敦经营一家叫做 CHINESE LAUNDRY 的中餐厅,这周见面时我们交流了她此前在云南驻地项目的经验、她的家庭食谱,以及在伦敦经营餐厅的体会,对本土饮食延续的看法,实在是很尽兴的聊天。
当我问到她如何用伦敦当地的食材去制作她的家乡食物时,她和搭档 peiran 一起研发菜品的方式启发到我:两个本土饮食经验不同的人,其实可以互相给对方的食物提供一个解构视角,将传统食物解构为食材、口味和口感之后,再就地取材寻找合适的方案。
我很能从 Tongtong 的表达中找到一种共鸣:在世界的范围内,中餐是一种本土饮食,而他们在国外所遇到的中餐并非味觉故乡,更接近一种建构于经营者与食客之间的味觉想象。所以她们选择通过食物创造自己的味觉故乡,去传递更接近本土的、真实的中餐。
我们做 Chinese Laundry 的一个热情,就是“怀念”。 那些在原始记忆里的感性味觉,带着温度,带着气息,带着层次质感,背景音的煎炒烹炸,笼子里的虎皮鹦鹉,楼下的豆腐脑叫卖,犹如通感修辞一样在大脑皮层温暖发酵。把那些感性的记忆揉出来,给我们的“怀念”一个软硬兼施的保存与分享。
相似的,在北京生活第十年,我最常遇到关于福建菜/闽菜的两种极端想象就是佛跳墙和沙县小吃。当本土饮食离开本土,如何能更好地就地取材、表达本土饮食的特征是我们都在探讨的问题。
结识的另一位本土料理人,江湖人称「东哥」,广州人,也是北京顺德菜老店「顺峰」的前主厨。第一次认识东哥是在北京的顺德菜饭馆「凤城汤厨」,印象颇深的一个细节是当晚他做了一大锅鸭肉煨的鲍鱼,有人见锅里的鲍汁香浓便说这汁一定很配米饭。东哥矫正说,如果是他会选择用米粉,因为米粉质地更干,适合吸附汤汁。听东哥的爱人说他在家煮面放葱也只取葱的中段,因为葱头的味道太重,葱尾往往又软塌不硬挺,需要都摘去留作其他用途。
昨日午饭后,东哥就要和爱人一起离开「被困」两个月的北京,返回东北家中。茶歇间隙我才和东哥单独聊起他之前的经历,得知他在来北京前,先在沈阳的顺德菜饭馆做了十年。我好奇地问他:「在东北做顺德菜和你在广东本地做肯定不一样吧?」
他说,「对,酱汁要更浓厚一些。」
「那这样会不会背离传统呢,或者说还是顺德菜吗?」我斗胆追问。
「当然是顺德菜呀!我的原则就是本味,酱汁厚一点但不能遮盖食材的本味。」东哥解释道。
几次观察和交谈中,我渐渐感觉到东哥虽然资历深厚,但他仍然是个对食材充满好奇心的料理人。他主张「本味」和主张「烹饪要做减法」,食材是他最重要的原则。他启发我在本土饮食这条路上,除了寻找本地独特的调味(如红糟)以外,尤其重要的还要定义本土的食材。

电视节目《厨王争霸》
Young:来自朋友推荐的一集电视综艺节目,是法国厨师和中餐厨师的对决。比赛是从双方的食材博弈开始的,比如当法方厨师拿走了中国厨师的花生油,中国厨师靠一块猪五花肉炼油仍得以顺利完赛。与此同时,看法国厨师研究如何处理北京本土的「麻豆腐」也很受启发。其实无论是中餐法餐,一个厉害的厨师是能对食材有准确理解的。
节目中也呈现了这些食材的挑选考虑,是由北京「四季民福」的餐厅采购经理负责的。他作为拿捏厨师烹饪难度的出题人,早就在选择各种食材时预想好了厨师要攻克的食材难题。这是全场我觉得除了厨师最厉害的一个角色。
播客《人是铁饭是钢》:聊聊福州菜和小家宴
Young:继《明日之路》后又上了一档和食物有关的播客《人是铁饭是钢》,这次和主播 Way 聊了聊福州菜和自己在北京的小家宴故事。张罗小家宴,自己有点无知无畏的态度,也会出现失败现场,但总归每一次的收获都很大。家乡的食物里有味觉记忆,而在异乡的饭桌上,食物的更深意义是创造记忆。

图:本周准备的暖冬小家宴菜单
播客《灰度上线》:从产品角度聊美食的标准化和多样性
Young:这是一档用产品思维来看世界的播客节目。比如将「火锅」视为一种产品形态时,是社交产品?流量产品?还是?将食物抽象化来探讨,是蛮有意思的思考训练。
台灣美食技術交流協會:#台湾的芋头味
Young:由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芋头食材出发,集结台湾农人、美食家和料理人共同对话的食材议题。推荐首先是有感于台湾对本土食材的挖掘深入和视角广度,再就是感受到本土文化传播、身份认同的建构也可以从一颗芋头展开。槟榔芋作为台湾主要的一种芋头品种,我是通过这个协会的 facebook 主页获取到的很多关于芋头的知识和创新料理的思路。
摘录两则台湾料理人对芋头食材的用法理解:
這次提供給各位的芋頭都是檳榔心芋,依序分別為 台中大甲、花蓮吉安、大甲大安溪,入菜的過程中用了哪些方法來調整質地與提升風味?
維:我在處理食材時習慣先蒸起來吃原味,了解食材前中後段的風味表現。這次拿到的大甲芋頭可能因為季節還沒有到,所以頭尾兩端的質地紮實,我拿來用蒸的做芋泥,雖然芋頭也可以烤,但因為烤焙處理後的芋頭味道會比較濃厚,和我想呈現的在地風味不太一樣,所以還是選擇用蒸的。而這次芋頭中段比較鬆軟,容易蜜漬,所以拿來做蜜芋頭。在蜜芋頭過程中,我還清酒,感覺會更清甜。頭尾兩端的芋頭 蒸熟後拿來打泥。另外,外皮並沒有採用義大利貝殼酥的做法,而是改以丹麥可頌派皮製作,口感會比較突出。另外,一般人認為油蔥搭芋頭的風味很怪,但其實烤焙過後,油蔥和芋頭的味道非常平衡。
請就菜餚構思要強調芋頭的哪個特性以及設計的靈感?
維:我自己是新竹人,在新竹當地有一個道地的古早味,是加了油蔥酥的熱芋泥,我們在地人很熟悉,可是對外地人來說這種搭配似乎很奇特,覺得甜芋頭和蔥酥的結合有所衝突,所以我想把兩者之間的平衡感做出來。外皮的部分,我的靈感來自於拿坡里貝殼酥,在義大利當地是以麵團和豬油做分層,但我改以可頌丹麥外皮,我希望這道芋甜品內在柔軟,外層卻意外地很酥脆,產生較為突出的口感。

从食材特性出发研究的芋泥点心

《1000小食报》#16 期发出后不久,小报迎来了第 1000 位读者。再次谢谢作为 1/1000 的每位朋友。如果你是新读者,也可以看看这封写给 1000 位读者的信来快速了解这份小报。
最近还收到两位江西朋友的「家乡来信」,一位是家乡在赣州的 Amanda 给我寄了一整箱的赣南脐橙,还有家乡在吉安的客家人 Kevin 收到家人寄来的本地小食(一种类似蔬菜天妇罗的小吃),也说等顺路的时候带给我尝尝。
这些对我来说真是很有意思的体验,线上的小报投递竟然收到了充满真实食物味道的回信。谢谢你们!
欢迎大家继续来信跟我分享你阅读《1000小食报》的感受和思考,我都会回信的!

图:Amanda 寄来的赣南脐橙

由 Young 编辑的《1000小食报》:
查看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