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小食报 #40「自由」是独裁者食物的调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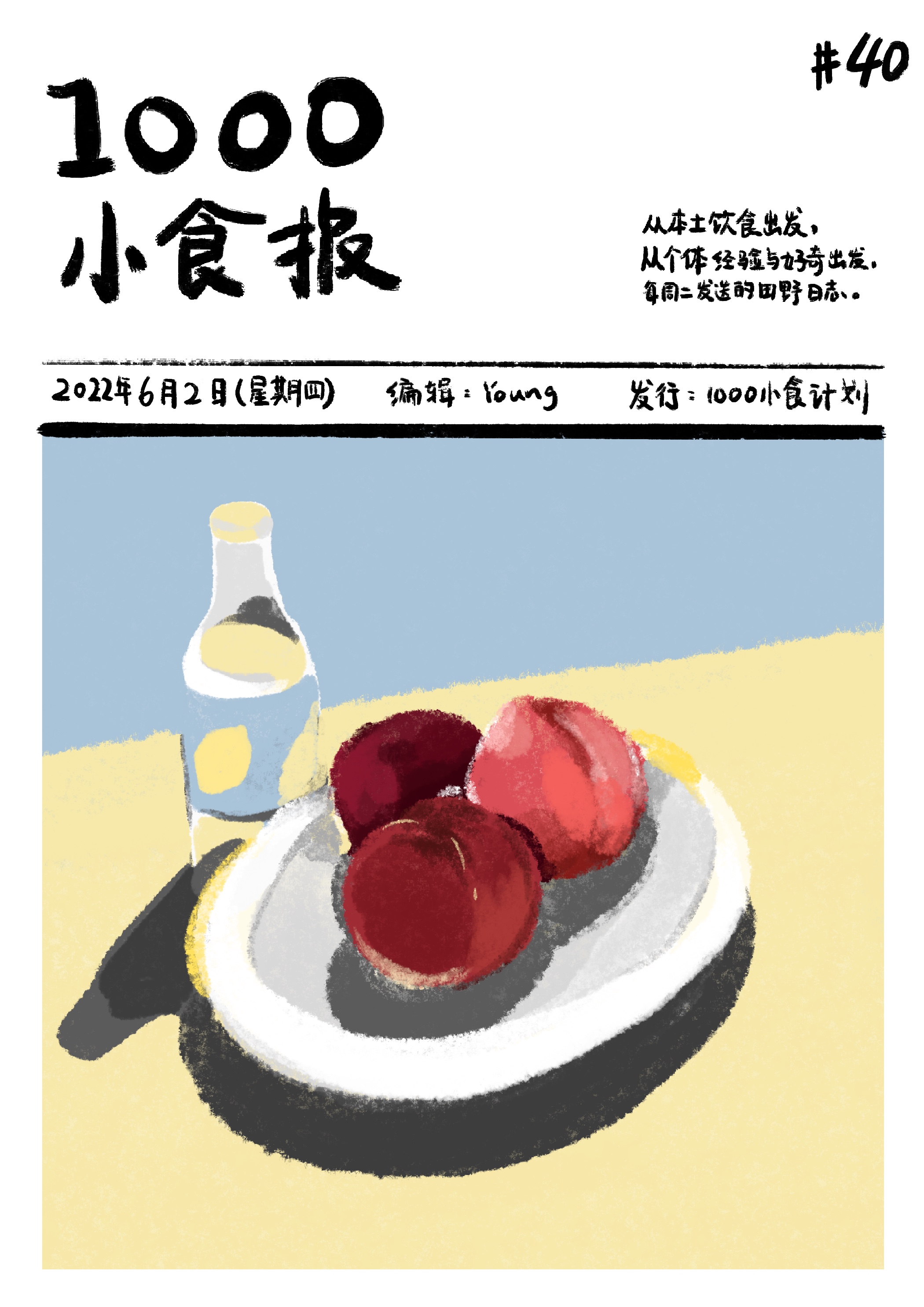
进入六月,北京和上海这两座超级城市像被同时被按下播放键,生活仿佛一如既往。「但有些看不见的永久变化已经发生了」,人像是被敲了一闷棍后,摸索着断片的记忆。
唯有记录让人清醒:记录会提醒我们,有的「自由」只是独裁者食物的调味料。
这个说法源于不久前在 TheAffairs 网站上看到的这篇书评,其中提到一种通过吃喜欢的食物来观测自己身心的「生活小窍门」,也佐证着食物作为一种投射时的坦诚:
前陣子有一則日文推特翻譯在台灣瘋傳,全文引述如下:我以前有一個學長,在做出重大決定前總是吃炸雞,被問到是什麼原因時,他說:「如果你喜歡的食物,吃起來還是很美味,那你的判斷應該還是正常的,對吧?」如果發現自己喜歡的東西不好吃了,或許你的身心現在很虛弱,你的判斷力可能會出現問題,這好像也不失是種生活小竅門。
摘自:一種在場又不在場的獨裁者調味料:「自由」
…
这周见了两位从封控了一个月的小区里获得「自由」的朋友,我也会向他们问出「这段时间会感到愤怒吗?」类似已知答案的问题,但直到我将话题引入食物,比如「小区还能点外卖吗」、「食物怎么送达家里呢」以及「连续做了 30 多天饭会感到烦厌吗」,我好像才更真实地感知到人在其中的精神状态。
其中一位朋友幸告诉我小区逐步收紧政策的表现:外卖由能送到小区大门口,到送到单元网格区域内,最后足不出户的阶段则再由网格内的社区工作人员统一送到家门口。相应的,外卖食物抵达后延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最终从下单到收取到食物的时间,她估摸平均在 3 个小时。
考虑到延时送达对食物造成的影响,她的采购策略变成了:购买「冷冻」的肉类而非「冷鲜」(送达的时候肉可能已经是自然化冻的状态,可以直接做饭用了);尽量避免购买草莓、蓝莓等容易在几轮周转中被磕碰烂的水果——这些在非常态生活中形成的饮食经验,提醒着我们食物存在的其他评价维度。
第二位朋友静林从居家饮食中获得的一大心得是家庭食谱的传承。他与我分享了母亲是如何通过手机镜头画面帮他看着锅里的油温,指示下入「过油肉」的时机,和豆角焖面的调味用量……然而在他看来,这两次几乎「手把手」的教学,最终的成果都不尽如人意。
因此他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亲自动手」的必要性——只有自己做过了,才知道那些「适量」和「少许」确实是出于一种应对具体问题和真实情境的合理表达,以及知道眼睛看会了的食谱,在真实的制作过程中还空缺着诸多细节。
作为参加过两期「在地厨房」的体验者,他在回顾作业中写道:
食物果然是时间的朋友,面对它,技巧、流程、工具,其实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相处。人和食物,只有在互相熟悉彼此的状态下,才能呈现出最好的样子。
所有的食物只有经过我们第二次、第三次,或者反反复复制作后,才真的会与我们产生联系——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经验」。
关联阅读: 1000小食报 #29 面的食谱源于手的记忆

图:和刚解封的朋友一同逛超市

五月初起,北京的餐饮行业就在疫情防控中陷入停摆。由于身边有不少在餐饮行业中的朋友,我多少能想象到其中的艰难。出于一个「记录者」的习性,我产生了一种身体力行参与当下的迫切想法:相较于言语上的关照,或者浏览「疫情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的报道文章,我希望自己能在与从业者一起行动的过程中,进行一手观察(哪怕只能看到局部),再将其中细微予以表达。
我向熟识的湖北菜小店「汪婆婆」家的厨子发出是否需要帮助的询问,很快便敲定了隔天去店里帮忙拍摄外卖视频的计划。过去两周中大约有三四天的下午,我待在只有爹爹、婆婆和厨子的餐厅里,一边和厨子演练着热干面的拍摄角度,一边随手接听闪送骑手的电话……
桃子和热干面
下午一点半抵达汪婆婆的店时,婆婆已经坐在长桌边,准备等我来了就给我做午饭吃。她递过来一盘色泽红润饱满的桃子,跟我说:别人说这是「胭脂红」,但我知道这是「石桃」。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桃子那么熟悉吗?」
婆婆的话匣子就从一颗桃子打开了——在接下来近半个小时的叙说中,我一边暗暗惊叹婆婆对种种细节描摹的语言天赋,一边拿着桃子等着下嘴,但直到婆婆的故事被中断,我都没舍得要发出声响去咬这颗桃子。
汪婆婆与桃子「结缘」于知青下乡。那天一群年轻人被生拉到一片郊野,知青们的住处作为周边唯一通了电的场所,要用婆婆的话形容:「夜晚整个房子就像一座孤坟」。负责管教的书记,在这些年轻人又悲又愤地要出走时,却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有桃子吃!」
后来汪婆婆被分配到果园劳动,在学会如何给桃子们均匀喷洒上农药「乐果」后,婆婆知道了:这些桃子根本吃不得。
但婆婆还是饶有兴致地与我分解给桃子打药的动作要领,比如如何在最少的频次中打足药量,由下往上喷洒桃子才不会生虫和浪费药液……她交待的细致程度让我以为掌握了这项技能(误)。
如果不是厨子到店里打断了婆婆的故事,我想这颗桃子会继续漂流在后面的人生旅途中。在这个沉寂的夏日午后,汪婆婆的桃子让我意识到,一定还有很多像桃子一样的故事被埋藏进这代人的劳碌中。

…
又一天拍摄日的中午,厨子提前在微信上告知我,将原定拍摄的外卖菜品改为拍摄店里出售的武汉热干面组合。随后他接连发来几条语音消息,即兴讲着他对热干面的理解:
我先记录上,我怕忘了:现在的汉口人口怎么着也有四五百万了。按照蔡家(蔡林记)后人说,一九四几年,他们家每天卖三四百斤面,按照一碗面给半斤算,三百斤也得卖 600 人。600 碗面,这高峰期怎么做得过来?由此「掸面」的工艺就诞生了。
「掸面」有多复杂呢?也没多复杂,说白了就是把面先煮到八成熟,然后迅速摊凉。在 40 年代那个环境中,最能摊凉的就是过冷水。我的儿时记忆则是一个大电扇。
所以说要想人前显贵,必须背后受罪。为什么热干面可以出那么快,15 秒一碗面。因为你的工作都做到前面了。我觉得「掸面」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早点变快了。武汉人本来性子急,等不及等不得,热干面快了以后,我们的粉也快,豆皮也快,面窝得先炸好,所有都得快——也符合当下这个年代。
用厨子的话说,小小一碗热干面其实是当代饮食表达的缩影:简单、极致、快。尽管热干面并非我的原乡食物,但出于对时代中饮食变革的共鸣,我也对热干面多了分共情。
在餐厅只能提供外卖的时期,厨子的外卖热干面做法是提供需要焯烫的掸面和酱料,由顾客自行拼装成热、干、面。尽管做法极其简易,但他还是耐心拍了条视频来讲「如何还原一碗武汉街头的热干面」。在我花了不到 5 分钟在灶台边复制完这碗热干面,突然对这碗面产生了陌生感:这本应存在于街头的食物,却出现在了家常饭桌上,人们在街头饮食中追求的「短平快」也渐渐成为家庭烹饪的趋势。
一些食物类型正在突破原本的边界,尤其在无法堂食的封控政策中,外卖中所覆盖的食物品类更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不免惊叹「这也可以做成外卖吗!」我还无法想象这种局面带来的长期影响,只能对简单保持着警惕:对烹饪和体验流程的简化,会不会也让我们的记忆与文化失去细节?
换个角度想的话,越是简单的食物,越应该去找寻它更复杂的叙事。

图:厨子准备的热干面视频「台本」和复刻热干面
让记录本身成为意义,让更多的记录发生
在最近对「90/90」口述计划的讨论中,队友说「让记录本身成为意义」——当下这句话有一下子突破阻滞的力量。对这场发生在 90 后与老年人之间围绕本土饮食的对话,此前有一些由意义出发的包袱:比如是否体现共创,是否能保留下原生语言,编辑方案是否完善,能否出版留存……
而「让记录本身成为意义」则回到最重要的起点:记录下来是最重要的。
「90/90」应该成为一种家庭食谱记录行动的代号,1000小食要做的是让更多的记录发生。参与讨论的朋友曹蔚形容「90/90」给人的感受,这是一片汇集家庭食谱记录的海洋。
…
找回「记录」的核心后,我更明确了这也是《1000小食报》实体版的核心设计主张。
我还想到,应该邀请正在阅读本期《1000小食报》的你,开始尝试记录自己的家庭食谱,也欢迎你将任何形式的记录投稿给小报,这对我和 1000小食计划都是极大的鼓励。

图:《1000小食报》设计手稿

专栏:离别与重聚,从南美洲丛林到华阳菜市场
食物随着环境和机遇演化,看起来不可或缺的主角食材在错位的演化中甚至会被逐渐取代,这一度冲击了我对食物传承的理解。我曾认为,食物的正统极大取决于食材使用的正确,这让当时我执着于菜谱上每一处做法的正确。
Young:对这段话有同感。就像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一直以「驴打滚」替代家乡的冬至簸荡「米时」;喜欢的北方小店大都是因为店里有一碗认真的汤——在异乡的人难寻家乡吃食,与其去吃与记忆中相去甚远的标签化的家乡食物,不如去理解塑造自己味觉记忆的真正由来,或者自己学会可以随身携带的家乡菜。这才是永远不离家乡味的办法吧!
我也强烈推荐这个由两位创作者板栗和核桃创作的饮食文化专栏!你不仅能读到他们对食物具有的奇妙感应力和文化联想,他们共同创作的配文插画也独树一帜。

文章:皮蛋为什么被大厨们争相解构?这个问题,要从一个四川小镇说起
喻波决定用一个黄金皮蛋,重现他小时候的风味记忆:他专门挑选了一种硬质的、颗粒较大的白糖,直接撒在皮蛋上。一是借着白糖的硬脆,衬托出蛋清的弹韧和蛋黄的软糯,不同的质感,让口感变得极为复杂;二是利用咀嚼白糖时发出的脆响,让它巧妙地成为「响声菜」,调动客人的听觉。
Young:阅读此文你至少会有两个关于皮蛋的智识收获,一个是皮蛋不同层次的叫法;另一个则是能清晰地理解皮蛋的制作工艺。进而可能会对皮蛋撒白糖的「大道至简」跃跃欲试。

一封给队友的信
五月,我拥有了一位「队友」——发生在「1000小食」计划独自上路后的第十个月。这是写给队友的第一封信,分享出来一来想庆祝我们遇见,二来想完整地表达一次我对「队友」的理解。
Hi 队友 T.Y,
在年初的一次采访中,我被问到对今年的希冀,当时回答的是希望能找到同伴/同路人。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喜欢与人在一起做事的。这一年里,无论是《1000小食报》的读者、一起发起「在地厨房」的合作伙伴,还是身边为我提供各种支持的朋友们,每个人都曾带给过我接力般的连结感。但直到我们彼此确认「队友」身份,我才发觉这是我从未建立过的另一种连结:
从我们面对面坐在桌子两侧,分享各自对「在地性」的理解到深夜;当我畅想着 90/90 的口述计划如何拥有完善的编辑方案时,你跟我说「记录就是它的意义」;收到《1000小食报》的读者回信时,我可以第一时间将收信的快乐分享给你;你开始加入我和曹蔚对「在地厨房」体验方案的讨论;我们基于各自的吃喝经验,一起出现在朋友的产品研发室;我开始创建一个叫做「成为队友」的日历,将与合作伙伴的通话约会、与小报设计师的勾兑日程,与调酒师的厨房实验安排同步于你……哪怕是像「麻婆豆腐体验」这类还没撇的草稿想法,我也可以在想法刚冒尖的时候就得到你的反馈。
即便如此,在刚刚「上场」的这段时间,我还是会不时向你确认:这是与你的人生主轴相近的事情吗?你对它会感到期待吗?
谢谢你每次都能认真回答并予我肯定。
我们都很喜欢「队友」这个称谓——相较于关系中的其他说法,它让我们遇到的每个朋友能更确切地理解我们在一块儿的意义。
我们曾在数次交谈中描摹过「成为队友」的感受,也让我想在这封信中与你分享我对「队友」的三种理解:
队友之间拥有底层的连接,而不仅仅是情感的支持:在我们的第一次深入交谈中,你就不吝与我分享「让人吃得更好喝得更好」的人生志愿。而我们也在后来一次次的探讨中,对其中的「更好」建立起共鸣。这是我们成为队友的基础。
队友是一种相对长期的关系:有一天和球队朋友看完球赛的回家路上,好奇问你「大家都是如何成为一支球队的球迷的?大部分人的球迷生涯中只会支持一支球队吗?」我联想到,信仰一支球队,与追随一种人生志业,都不是可以轻易扭头转向的选择——毕竟二者都是要人足够赤诚投入其中才能感知到幸福的事情。
队友是可以毫无负担袒露自己短板的人:在促使我们成为队友的那晚交谈中,最令我踏实的时刻是当我们说出那些各自不擅长、甚至感到怯懦的事情。这让我们更明确能为彼此提供的支持,也拥有了「把球交出去」的信心。
在《1000小食报》里夹带这封「给队友的信」,希望不会让你感到唐突和压力。小报作为记录着「1000小食」每一步进展的田野日志,也是从我的生活中「生长」出的完整内容表达,回顾最近一段时间,拥有队友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谢谢你在这个时点出现,让我有勇气和底气去追求「1000小食」和「在地厨房」更完整的样子。
队友:Young
2022/6/1

由 Young 编辑的《1000小食报》
查看近期投递的小报:
关于「1000小食」
为本土饮食文化在当下的传承探索新的传播方式
媒体报道
Local本地:「厨房里的人其实是很孤独的」
好多現象:饭桌上的家〡ZINE CHAT
LOHAS乐活杂志:两代人的厨房,家宴里的记忆与爱
Alex绝对是个妞儿:她说喜欢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