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小食报 #51 何以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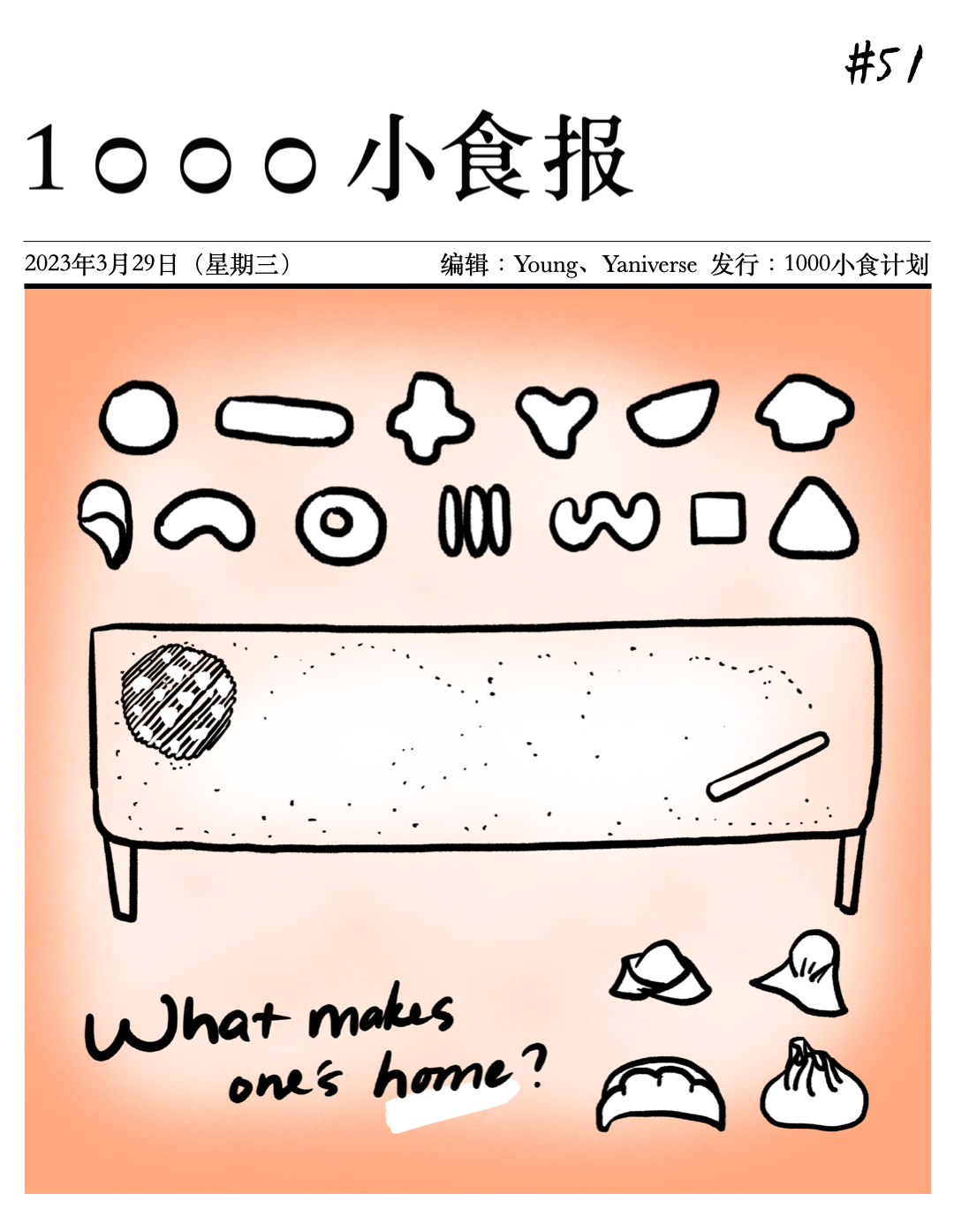
在白昼终于要和黑夜平起平坐的日子,我决定从写「周记」开始恢复一些书写的日常。以及今年围绕「家」策划的展览也进入了内容筹备阶段,接下来也会在小报里记录下这场展览筹备过程中的一些感受(上一封通信中分享了「今年最想做的事」,随时欢迎你来信与我交流想法)。

这是以一场持续 3 小时的访谈开启的一周,但访谈的准备大约从一个月前就开始了。
访谈对象是一位家庭食谱记录者,她的名字叫做春艳,生于 70 年代。春艳作为知青的孩子,出生在新疆,童年与外公外婆共同生活在四川,到了上学的年纪,被送回父亲的故乡南京,但毕业工作后不久,她为自己的爱情来到法国。从 20 岁出头离开父亲的故乡南京,今年已经是春艳在法国生活的第 22 年——与她的法国丈夫、还有两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一起。
去年「一席」演讲发布后不久,我的邮箱收到了春艳的来信。她在这封不长的信件中快速描摹了她的家庭迁徙轨迹,还提到了对她而言意义非凡的食物:南京小汤包。摘自春艳的邮件:我能想到孩子们最喜欢吃的一道食物是小汤包。在南京只会在街头小吃店才会买到的,家里基本不会去自己动手做的,因为在孩子们小的时候,我带他们回南京,爸爸因为是回民,不允许在家里吃猪肉,所以妈妈会带着孩子们去外面吃家里没有的东西,那成为孩子们最深的记忆。我尝试着在法国给他们复制,没有那么美满,但也一点点成型。回到中国,一下飞机,孩子们在机场就嚷着带他们去吃小汤包,然后他们却很失望地说,没有妈妈在法国做的好吃。而我在法国费劲地包出不破皮,能有汤汁的小汤包端给我的孩子和丈夫时,我的孩子会小心翼翼咬开一个洞,倒灌进一些醋,冷却汤汁,很享受地吱吱地吸完汤汁。而我的丈夫直接拿起刀叉就把汤包分成四块,说是汤汁太烫了,不然他无法下嘴。毕竟法国人吃饭是不允许发出吮吸的声音的。
「到底什么样的食物,才能够代表我的家?」
收到春艳的来信后,我很快就联系上她。在我们并不频繁的微信对话中,我感知到她对自家的跨文化饭桌,始终保持着敏锐的觉察,以及在这样的语境中积攒下的丰沛情感。当然,她也不无忧虑地关切着我要如何支撑起「寻找1000位中国家庭食谱记录者」这个远超个体力量的项目。所以,她能想到最实际的支持,就是尽力将她的故事分享予我。
我们的对话发生在星期一,我的北京时间下午 5 点,法国雷恩时间的上午 10 点。春艳在去年拿到法国厨师职业培训资格证后,就进入了当地一家米其林一星餐厅工作,负责前菜出餐环节,每周工作六天,周一是她唯一的休息日。这是我和春艳的第一次「见面」,这一面我们聊了三个小时。在长长的对话中,春艳向我讲述了她第一次在邮件中选择分享「南京小汤包」背后的细致考量——到底什么样的食物,才能够代表我的家?
首先猪肉馅的汤包在春艳的回民父亲家族中是个禁忌,但父亲并未要求春艳和母亲彻底断绝对猪肉的念想,而是提出只要不在家中吃的要求。于是南京小汤包成为春艳童年与母亲最珍贵的外食记忆。
与法国丈夫一起生活之后,两个中法混血的孩子很快跟着春艳学会吃汤包:用筷子小心地把汤包从笼屉上提起,稳稳放在瓷勺上,嘬开一小口,罐进醋汁冷却内馅中溢出的油汤,吸吮完汤汁,再吃剩余的皮和馅。而法国丈夫则在盘中将汤包用刀切开,放出汤汁,直接吃剩余的皮和肉馅。在讲究餐桌礼仪的法国餐桌上,吮吸汤包汁水的吱吱声则是例外。
春艳选择南京小汤包来代表「家」,不是出于身份认同,而是其中蕴含着她对「家」内核的理解:春艳:他(指法国丈夫)可以包容我们吃东西稀里糊涂地发出声音,那么我可以包容他不能够欣赏汤包里面汤汁的精华,因为口味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能在口味上去包容别人,那么我们家里很多事情就都去包容,会去包容别人。当时我选择(南京小汤包)这个题的时候,更多是看到了丈夫和我们之间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今天谈起来,我在想更多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包容,尤其是新建的一个家庭。就像你提出「何以为家」,你说原来我们的家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现在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上海、去北京,然后我们又和不同地方的人结合在一起……这些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当我们没有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们在当地的结合是大同小异的,「包容性」就没有显得那么重要,因为大家都很相似。其实说起来,我和丈夫能做到的包容比两个中国人之间的包容更容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俩不同,所以我们去接受了对方的不同。但如果两个中国人,可能就没意识到我们(原本)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口味,不同习惯,我们总是要求对方来适应我们,而不是去理解对方。

图 / 春艳在法国的日常家庭饭桌(由访谈对象提供)
「我的记忆,不用也成为孩子们的记忆。」
为了这次访谈,春艳时隔一年半再次制作南京小汤包。
而在与她一起回顾这次经历时,我才了解到一个人复刻久远的家乡味道时需要承担的包袱:你要如何面对与记忆中味道的差距?又如何接纳这距离无法弥合的现实?
接着,春艳向我完整讲述了这一次制作汤包的特别体验和收获。春艳:这次做小汤包,一开始我也很紧张,一年多没做了,我能做成什么样?而且我从超市买来包汤包的皮,也不是很合适,我也还没控制好(自己和面的比例)。我突然想到,身边有一位中国老人跟家里独生女过来养老,他们的女儿很喜欢吃肉皮冻,每次做他们就问我借豆浆机,说用豆浆机做皮冻很容易,然后他每次也会给我一些。而我妈妈原来教我要自己用肉皮在锅里熬。于是我灵机一动,我可不可以把他做的肉皮冻调在我的肉馅里,这样汤包不就有汁水了吗?试了一下,很成功也很省事。我又继续分解(汤包),因为我不是北方人嘛,包包子的手法也是在(法国)学的,也不是很有技巧,但我会经常包饺子。我想我要吃的就是一块皮包着馅,馅里面有汁,那么可以把它包成包子的形状,也可以包成饺子形状,而且包饺子的时候,我可以放更多的馅,包子我包得不是很好,放不进去的很多馅。当我把小汤包化解成带汤汁的肉饺子后,我的压力一下子就很轻了。
或许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极力接近的味道,仅仅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味道时,也会放下许多对「正宗」的执念。而春艳这一次将南京小汤包变成包「带汤汁的肉饺子」的解题思路,也与她过去七个月系统地接受法餐学习不无关系。春艳:在餐厅工作的时候,也常看到这边米其林厨师的宣传,或者他们的提法很多是「记忆中的味道」,我曾经觉得这只是一个煽情的说辞罢了,然而在做汤包给孩子们吃的时候,我一下领会到他们的意思。我在做的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东西,但我的孩子们吃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妈妈的记忆——不会想到是因为外公不允许吃猪肉,只有出去才能吃到的快乐,不会有经历一个月等待才能吃一次的这种(感受)。他们不再会有我的这些记忆,他们的记忆是我做出来之后,这个味道他们很欣赏,觉得好吃。有时候我想这就够了,我不希望把我所有的记忆都要求他们去跟我同步感受……

图 / 再次复刻南京小汤包的记录素材(由访谈对象提供)
「我的家难以定义,但是我知道我有家。」
第一次收到春艳的来信时,我从中读到的是她的「家」难以定义:「我希望加入你们的活动,但是仿佛又无法给自己定位。家乡如果当下我定义为南京,可是她的变化已经是我无法体会和想象的了。」
而这次直接而深入的访谈中,我则强烈到「家」的复杂性甚至让人产生了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的回避。我很感谢春艳,她坦诚地与我分享了她的回避、感到的别扭。而在我们共同厘清「家」概念的过程中,我们也建立起了信任与更深的共鸣。春艳:我好像不知道在哪里定义我的「家」,当你提到「家」的时候我就很困难,因为现在我的父母他们也没有在这(法国)定下来,他们来了之后不适应,然后他们又回去了。那么说「家」的时候,我不能够定义我的家在法国,因为我的父母还生活在中国;那么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又不能定义我的家在中国,因为我的孩子、我的丈夫在这。所以这就让我去回避「家」这个(概念)。但是当你讲到最后(前面与春艳分享我希望呈现的「家」)我理解了,我就想,小样她在寻找的是整个社会、家庭变化过程中间,家的真正意义。如果我问自己家位置在哪,我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知道我有家。所以当看到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问自己我该用什么去表达我的家。我很感动你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寻找我们来自哪里……
12 年前,我来到北京上大学,也从那时开始离家。而现在我也不能确切回答,再过 6 年,我会在哪?我会成为「春艳」吗?如果有一天,我也像春艳一样很难定位自己家的位置在哪,我希望也能和她一样坚定地说:但是我知道我有家。
何以为家
春艳的访谈也是筹备「何以为家」展览的一部分前期工作。当我回味着饺子形状的南京汤包故事,脑中也渐渐浮现出将它呈现于展览中的主意:
就像许多北方家庭都有自己惯用的饺子捏塑手法,这本身是一种「家」的印记;当春艳改变了记忆中南京小汤包的造型,这不正是一种对家的「重塑」吗?那么,在展览现场「捏塑」面团也可以成为观展者与故事互动的方法。无论捏出的是褶皱包子,还是元宝饺子,它们都是我们亲手创造的家的形状。(本期封面:展览互动概念插图)
这一周和另位策展人刘露蕊还一同准备了展览的介绍规划,接下来我们会分头准备展览作品,同时也在继续寻找着展览的合作伙伴。如果你有意向为这场展览提供支持,可以回信告诉我,我也将提供这场展览的介绍资料。

图 / 周末在露蕊家吃到的「认真家宴」

播客《饭桌上的家》近期更新
分享一下最近的几期播客节目,以及我们的节目已同步至苹果播客、小宇宙、Spotify、网易云音乐、QQ音乐平台,欢迎收听!留言!
【#8 一直在追求一颗完美的蛋】鸡蛋,是饭桌上的阳光空气,是很多人的厨艺启蒙,又是很多人终其一生寻找的完美化身。本期节目,我们将话题聚焦于鸡蛋,除了庖丁解牛式地聊了聊炒鸡蛋,我们还分享了各自心目中的完美鸡蛋。
【#7 聊「厨房里的男性」,就是聊「厨房里的女性」】「好男人」、「顾家」、「爱妻」往往成为男人走进厨房时会获得的赞誉——但更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在厨房这处家务要地的存在感实在稀薄。而在厨房里看不到男性的时刻,都是女性在面对烈火烹油,却被大多数人视为一种理所当然。我很想知道,当我们的同辈人走进厨房承担做饭劳务时,他们的动力发生了什么变化?于是我和 8 位朋友通了话或面对面聊了聊:「他们」作为「厨房男性」的亲身体验、或「她们」家庭中的「厨房男性」。听完后有对这项职责分配不公平更深的理解,也有些鼓舞、有些信心。

庄祖宜《餐桌上的人间田野》

Young:这是庄祖宜记录于过去三年的一本家庭食谱合集,原原本本地摆出了她一家人的餐桌菜色。因此不同于之前一道菜一道菜的食谱,新书采用了一餐饭一餐饭的写法,以「家」为对象,以「搭配」为核心。也因此看见「番茄鸡蛋汤」这样的菜色穿插于「椒香牛肉大饼」和「老虎菜」之间,「蓑衣黄瓜」与「孜然肋排」、「芹菜豆干」一同上桌。
詹宏志给这本书的推荐序言中写道:「我们不一定要遇见天翻地覆的变故才珍惜家庭,我们也不一定要遇见疫情才彼此扶持,我们只要每天回家洗手做晚餐,家人一起吃饭,我们也许就得到某种幸福美好的保证……」

邮件通讯及独立出版《1000小食报》
🔍 https://1000xiaoshibao.com/
联系方式
个人邮箱:[email protected](添加微信请私信联系方式)
如何关注「1000小食」
微信公众号:放羊姑娘(记得星标呀!⭐️!)
社交媒体 ID:小样 Young(即刻/小红书)
邮件订阅《1000小食报》(🔍 young.zhubai.love)
播客订阅《饭桌上的家》(🔍苹果/小宇宙/网易云/QQ 音乐Spotif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