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小食报 #54 剩食翻做:让今日的你完全打倒昨日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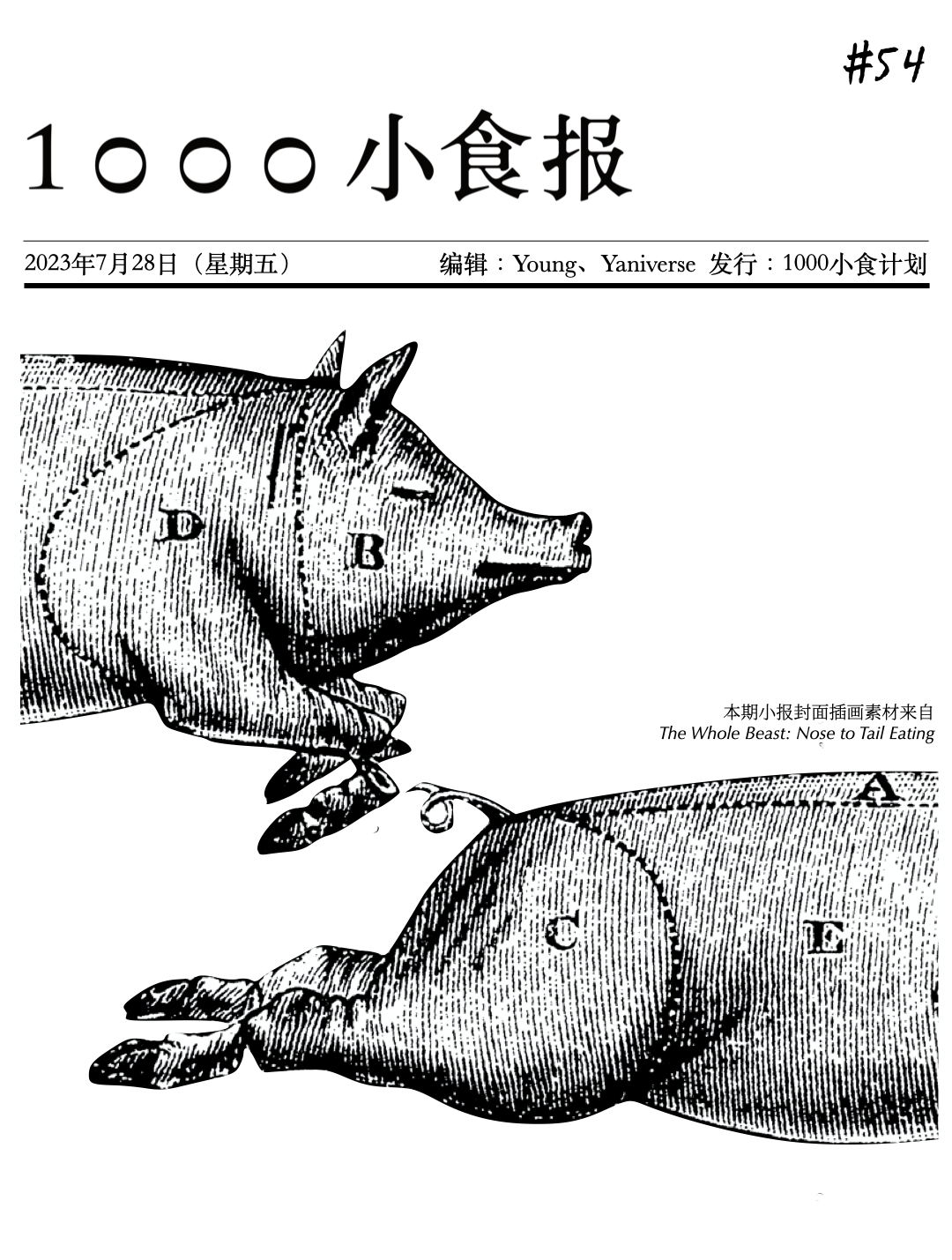
我很喜歡剩食翻做,因為它充滿了驚喜,更能讓今日的你完全打倒昨日的你,很有挑戰性。——「饒雙廚房」主理人饒雙宜
打开冰箱,发现为昨日家宴准备的食材边角料,思考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今日饭桌新菜色的解法——若由此发掘出消耗冰箱深处的味噌、或用一次总会富余的调味蔬菜的办法,这大概就是「饶双厨房」主理人饶双宜所说的「今日的你完全打倒昨日的你」。
最近的生活中,我常常有「打倒昨日的自己」的念头。
七月,在阿那亚金山岭社区,我作为分享嘉宾参加了阿那亚「放空假日」和创意活动家边忭发起的 NTT 项目。NTT 是 Nose-to-Tail(从鼻子到尾巴)的缩写,这一说法最早由擅长烹饪内脏的英国厨师 Fergus Henderson 在 1999 年提出,2004 年以《The Whole Beast: Nose to Tail Eating》一书在美国出版,获得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Nose-to-Tail 也从一位厨师的烹饪理念,逐渐演进成国际餐饮业中「食材零浪费」的代名词。

图 / Fergus Henderson《The Whole Beast: Nose to Tail Eating》
当边忭与我阐述她对 NTT 的理解,我脑中最先冒出的中文词汇是「物尽其用」,进而想到去挖掘本土饮食文化中食材边角料利用的主题。准备这个主题,我不妄想汇集「食材边角料烹饪大全」, 但也不希望「物尽其用」的生活智慧只停留于过往,因而一面搜集着各地饮食中适合佐证的食谱,一面不断追问自己,人们化用食材边角料的普遍思路是什么?

厨房边角料,也是记忆里的边角料
边角料无处不在,而能在厨房里发挥余热的是少数。
对家庭厨房的新一代继承者而言,要是不具备宽广的食用经验,或者因匮乏经历而遗留的生存习惯,许多厨房边角料几乎等于「不可食用」,也因此不被看见。
作为其中一员,如果不是有读者专门记录下家庭食谱,我不会知道茄子的茄蒂和茄萼可以裹面糊做成风味小食:

图 / 家庭食谱记录者畅所记录的「茄子把把」
那位记录下外婆独创的「茄子把把」食谱的读者,也与我分享了这样一段记忆:关于茄子把的童年画面,就那一次:我想外婆当初剥下的肯定是完整的茄子把,因为成品很大只,而且估计只有两个。出锅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吃掉了一个,外婆还派我给对面楼里的小伙伴送了一个,可能正是这一路激烈的内心斗争,我才把这件事情记到了现在。
其实,茄子把把不仅仅是食材的边角料,也是记忆的边角料啊。生活中还有许多食材边角料,常常以一种不起眼、不显形状的方式照料过我们,直到某段记忆被唤起,我们才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去年夏天,我一直在寻找童年记忆的一味消暑「凉茶」。它有什么特别呢?无他,就是一种模糊的甜,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我难以辨识的甜味来源,成了心中的痒。我从父亲那要来本地凉茶的常用材料,有菊花、荷叶、甘草、麦冬,用开水一一冲兑,皆非所寻。
直到偶然在一篇民间文章中,看见「胡萝卜」和几味凉草的名字一同出现,我突然反应过来:原来小时候炎炎夏日里的甜意是胡萝卜水的味道!又因是母亲一直负责煮胡萝卜水,所以我没能从父亲那获得答案。后来与家乡友人分享这一段记忆,他告诉我他们家也煮胡萝卜水,不过用的是胡萝卜皮。
和胡萝卜水一样,许多被利用的边角料如果不经过刻意辨识,我们早就习惯它们的存在。
比方说福州人家庭厨房里不可缺少的调味品:红糟。红糟是本地酿制黄酒「青红」的产物,说是边角料也不为过。糯米与发酵引子红曲米共同反应后,酒缸里会产生鲜红的酒液和发酵反应后全红的糯米残渣,红糟即残渣的部分。红糟的风味中有酒香,也有发酵产生的醋酸。在调味中使用,常与福州菜里容易泛滥的糖互补,或与猪下水、山羊肉等肉食烹调,以香醇化解腥膻杂味;也作腌料和着色,比如做糟鱼和糟鸡的时候。
红糟在本地的用途如此广泛,可我却很难在离开本地的福建菜馆里找到这一风味。相较于红糟口味难以适应大众市场的解释,私以为原材料的生产逻辑是更关键的因素:
福州人家里的红糟从哪来?或许本地人会告诉你,是从家里自酿青红的亲戚或邻里那分得的;若只取红糟风味而不取其色,工业生产的调味品中已有接近其风味、品质也更为稳定的「福建老酒」;而江浙地区同样以酒糟为原料制成的糟卤调味汁,则占据更大的外地市场。对比之下,红糟的生产仍未脱离副产品的逻辑——也正因此,即便烹调历史悠久,本地红糟仍保留着一种未被开发的天然香醇,凝聚着地方对「物尽其用」的精妙理解。

图 / 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第四季中福建红糟的片段
不是不可食用,而是不敢联想
老实说,从小到大没有人教我应该如何择菜。所以当友人将一整把空心菜塞在我手中让我择,我只好凭着记忆中家人择菜的画面,手法犹疑地给菜杆「把脉」,将嫩与老的部分掐分开。后来和男友一起做饭准备青菜,两人偶尔也会因到底要保留多少菜杆和纠结一番。我想,绝大部分食材是从择菜开始成为「边角料」的。
准备 NTT 分享会之前,我在朋友圈里征集了一番家庭食谱中的边角料,零零总总汇集了:芹菜叶炒鸡蛋、炝炒花菜梗、番茄炒空心菜梗、咸鸭蛋炒空心菜梗、腌制韭菜花、炒莴笋叶、柚子皮蒸排骨、西瓜酱……这些往往被弃置的食材部位,其实只是缺少合适的烹饪方法——或者说,人的联想能力。
至今觉得空心菜梗的最奇妙做法,是将其切碎后和碾碎的咸鸭蛋一起炒,瞬间化身下饭菜。前些天自己又做了遍,一边细细咀嚼一边揣测,重庆友人的外婆在创造这食谱时的联想到了什么:是空心菜本身特殊的盐碱风味?还是也有耳闻南方的腐乳、豆酱和虾酱做法的空心菜?
查找资料中,令我惊奇的还有顺德菜里将「柚子皮」的粗料精做的食谱:柚子皮需要刨去最表层的青黄色,只留下白色海绵状的表皮,再将果皮焯水、反复浸泡、沥水,彻底去除柚子皮中的苦涩后,它才能成为一种食材。有着肥厚松软质地的柚子皮,与浓汤一起煨煮,通过借味产生一种「非肉胜肉」的味觉体验。还有柚子皮菜色,甚至连脂肪浓汤都不用,直接将柚子皮挂面糊炸,再在糖醋汁里滚一圈,直接地指向了厨师对肉的联想。
在家庭厨房里,食材边角料还可以成为本土饮食和世界料理的融合开端。
比如常见于西式烹调中的蔬菜高汤(Vegetable Stock)就可以使用两三顿饭收集下的蔬菜边角料一次性制作。蔬菜高汤不仅可以作为省力熬煮的面条汤头,还可以加入其他调味,做成蘸汁、沙拉酱汁,甚至可以适当替用为炒菜时热烹的调味汁。
用同样的食材翻做料理,中西方法的切换也会更为有趣。美食作家韩良露就在自家实践新春剩菜变洋食,从而变化出了乌鱼子意面、焗烤白斩鸡肉配蔬菜、油炸酥皮年糕,摘引一段文字来证实这些剩菜的吸引力:先以臺式餐桌上過年常有烏魚子為例,一旦煎或烤過並切成片,下一頓再加熱吃,魚子油潤不再,美味大減,一般會想到的,常是拿來炒飯,我則喜歡將之切成小粒或磨成粉狀,加橄欖油、蒜頭,拌義大利麵,最後加一小撮青蒜絲點綴兼提味。這做法可不是我異想天開,愛吃烏魚子的原就不限臺灣人,西西里、薩丁尼亞、威尼斯、普羅旺斯和希臘等地中海沿岸地區的老饕,也都嗜食此味,各自都有用烏魚子製作的當地特色菜。
受韩老师启发后不久,我就将冰箱里收拾出的一小角马苏里拉芝士、一撮罗勒叶、1/3 颗莲花白和半颗洋葱,做成了有着别样风味的「糊塌子」。

图/用蔬菜边角料制作蔬菜高汤,食谱来自 thenewbaguette.com
杂烩的余味
本土饮食文化中,「物尽其用」观念反映最深切的两类料理:一类是「下水」,即食用的动物肌肉以外的身体零部件,或用内脏料理指代;另一类就是「杂烩」,其中又分将食材剩余边角料汇聚起来,化零为整的做法,和已经走向历史舞台的剩菜、熟食杂烩。
父亲聊起 90 年代前的本地宴席,总会惦记一道十味杂陈的宴席余味「拉杂炣」——宴席结束后,主人家会将桌上剩菜汇入铁桶中,重新烧开,分予自家人和亲近的邻里。我循着「拉杂炣」搜索,发觉许多地方都存在着类似的剩菜杂烩:北方有「折箩」、「渣菜」、台湾有「结菜尾」、绍兴话称「阿龙」、河南人比作「下山虎」……这些食物现在大都退居历史,偶有出现的,也是现烹十来道菜再合一起。
杂烩做法与当下讲究精确调味的烹饪理念背道而驰,那么它的独特之处到底为何?
我想起父亲提到的一个细节:虽然每次杂烩的剩菜依宴席不同都有区别,但合起来的味道又都很像。杂烩之杂,不是酸甜苦辣咸鲜中的某一组合,而是杂陈之味,有人称为「奇味」,虽不好说是奇特多一些,还是奇妙多一些,但总能在其中大致感受当地人最热衷的调味模式。
杂烩之烩,指熟料加水翻煮,如今已不再适用于烹制剩菜,只在家庭处理剩饭的做法中被保留下来。最典型的就是「烫饭」(有的地方称「泡饭」),将前夜剩下的米饭加水或高汤,煮至米粒开花,还可下入青菜和肉丝。类似性质的「豆汤饭」也成为了四川人对残羹冷炙的眷念:豆汤饭,看起来很像是耙豌豆烧了一碗浓汤,没吃完,第二顿加点盐煮开,再把剩饭舀一碗进去。所以它很便宜。解放前它就是成都快餐的代表之一,贩夫走卒是豆汤饭的主要客群。
杂烩的另一独特之处,大概也在这种让人吃得唏哩呼噜的味觉记忆里:翻做的食材身段绵软,浸入隔夜入味的汤头中,面饭、菜、汤烩为一锅,让人无须咀嚼细品,吃到一口就会在身体中升起饱足的感受。
当杂烩不杂,食材边角料未见得会落入杂烩归宿,杂烩余味是否也在三年的抗疫宣告结束时消散?
翻新昨日的自己
这期的小报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周,每次开启文档续写之前的段落,都要面对一次昨天的自己——常说万事开头难,但续写也不总是酣畅淋漓的体验。期间不时自问,明明分享会都结束了,你为什么还要写下来?
作为回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认为对「物尽其用」的思考应根植于当下日常,绵延才有力量。提出《挖掘厨房与记忆里的边角料》这一议题,更希望它成为探寻本土饮食文化中「物尽其用」理念的开端。书写下来是为了更多人能想起曾存在于自家厨房与记忆里的边角料。如果你真的想起来,请直接留言或回信告诉我。
本篇提及的「油炸茄子把把」家庭食谱,来源于一年前发起的寻找1000位中国家庭食谱记录者的计划,它也成为启发我深入挖掘这一主题的起点。由此想来,家庭食谱的意义也不仅作用于家庭与个体,它也作用于我们对当下生活的理解。家庭食谱记录者的征集计划仍在进行中,欢迎投递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向我介绍你和你想要记录的家庭食谱。
写作过程中,我也反思「零浪费」和「可持续饮食」等理念的传播:在日常生活中促发人行动的到底是什么?
不是理念,那么是恐惧吗?对尝过救荒粮草滋味、或者在疫情期间领过蔬菜盲盒的人来说可能是;而我更相信的答案,是人要创造,要挑战,要不断翻新昨日的自己。

图 / NTT 餐酒对谈会现场照片
延伸阅读
- 阿那亚 NTT 项目介绍:放空假日×Nose to Tail 玉米的「物尽其用」之旅
- 韓良憶:大手張羅,化傳統成日常
- Helen Veit:剩菜经济史(原文:An Economic History of Leftovers)
- 博客:饒雙宜—饒雙廚房
- 饒雙宜:如何在疫情下食多餐
- 尔雅:豆汤饭,四川人对残羹冷炙的眷念
- 出版物:《好東島:酒黃・糟紅・田綠》
- 网站:Nose to Tail Recipes
- 食谱:How to Make Vegetable Stock From Scraps




